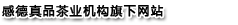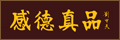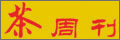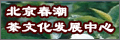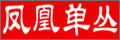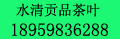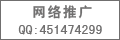商品搜索
首页>往期动态>详细信息
茶的淬炼
|
日期:2014-04-12 作者: 来源:东方早报 |

炒茶技师樊生华(左)在家中炒茶,他发明了一套西湖龙井的炒制手法。
再好的茶叶刚从山上采摘下来时也顶多是片完美的树叶,经历了茶农手中的道道工序,方能在人世间淬炼出最上品的味道。
当年沉默寡言的樊父将儿子的手按在了发烫的炒茶炉里,那里有散发出茶香的柔软叶子。樊生华第一次吓得把手缩了回去。父亲像是宣告判决的法官,“伢儿啊,你以后只好靠我这个手艺吃饭了。”
少年时代的樊生华并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炒茶手艺日后会赶上当年的父亲。
炒茶的手感
3月18日,新茶开采的第一天,今年首批西湖龙井的鲜叶下了老焦山。虽然比去年同期晚到了十来天,但它们可能是这个春天里西湖龙井茶产区最早采摘成功的鲜叶。
当天,乘着天亮,5名村民上山采了茶。没有游客的探访,也未有茶商的守候。采摘的高峰期仍未到来,村口也没有出现江西、安徽、河南等地采茶工的身影。
刚凝聚在叶尖的露水又悄然在春阳里蒸发,茶农们用两个指尖夹住这样的鲜嫩茶叶,轻轻放置在了背篓里。
背篓口小,篓身大,这样刚采的新鲜茶叶能避阳,又能装得满。上午的采摘一结束,茶叶随后摊到了樊生华家中的院子“阴晒”,即避光干燥。前日的一个晚上,回到家中的张建芬清洗了晾晒西湖龙井的竹篾。光一个上午,茶叶就摊放了4张竹篾。
2个多小时后,这批“西湖龙井43号”的新茶种将进入发热的炒茶锅里,叶身上的水汽热腾腾地冒了出来。
这一工序被称之为“杀青”。“杀青”位于采茶和晾晒之后,它是“炒茶”的第一个步骤。
当日下午,樊生华接连“杀青”,他手中抖落的龙井茶叶在炒茶锅里翻腾着。新鲜的茶叶富含水汽,茶叶和100多摄氏度的炒茶锅一接触,就发出吱吱的响声,炒茶人不停地从锅里抓起茶叶,手腕轻轻抖动,茶叶又重新掉回了热锅里。
在“杀青”的15至20分钟期间,茶叶不停地往来于手掌和锅中,像是一阵春雨落在瓦片打出滴答声。等到“雨声”渐歇,失去水分的茶叶便干上了七八成。
可龙井就是龙井。
“杀青”后的龙井,两片芽和一张芯仍是舒展的。
茶农也名不虚传,在他们眼中,“杀青”后的龙井仅仅“热了身”,芽和芯需要“放松”,因为接下来还有回潮、煇锅、收灰等8道工序等着它,整一过程统称为“炒茶”。
只要西湖龙井的鲜叶下了山,接下来的炒制也来不得半点停歇。历时最长的一次“杀青”,樊生华不分昼夜,“杀”了三天三夜。
樊生华从父亲那继承这一手炒茶的手艺。但那时候的“旗枪”叶面宽大,日后的“龙井”越发“玲珑”,口感和品茶人的口味也逐渐改变。
含水量约75%的鲜叶,经过一道道工序,最终炒制成含水分只有6%左右的干茶。
炒制一斤的特级西湖龙井,约耗时8小时。
当年腿脚不好的樊生华只能坐着炒茶获取生产队的工分;进城寻工又屡遭拒绝,自主经营当茶商又不够本钱,于是专心“炒茶”。
樊生华的经验证明,茶农的身体部位中,比腿脚更重要的是“手”。他发明了一套西湖龙井的“炒制手法”,主要有10个动作,分别是“抓”、“抖”、“搭”、“拓”、“捺”、“推”、“扣”、“甩”、“磨”、“压”。
这10个动作之间既区分又连贯,配合火候时既可以先后进行,也能同时发生,诀窍在于“茶不离锅,手不离茶”的手感。
樊父在60岁以后就渐渐炒不动茶了。桐坞村炒茶人一旦上了年纪,基本将之前的手艺用在了做饭烧菜上,用以招待“采茶季”涌入村子的外地采茶工。
当老父将越来越多的好菜放在樊生华的面前,炒好的茶甚至用不着出门就有茶商来收购时,樊生华知道,光论炒茶技艺,自己超过了年岁已大、体力渐衰的父亲。
樊生华一心想着炒茶,因此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也“炒”出了“大师”的美名。
西湖边的斗茶
虽然西湖产茶区已经统一称之为“西湖龙井”,其间出产的龙井因为地势环境和炒制工艺上的精微区别直到今日依然存在。
只有内行人才能读出这隐藏于舌尖、涵盖了各自出产的山头、生与熟之间的炒制工艺,山水还是自来水泡制等一系列富含在西湖龙井中的信息。
满觉陇的茶农杨忠伟前年春天参加了一场西湖炒茶大赛。比赛前一天,他用湿毛巾搭了一下茶叶。
比赛的当日,“评茶师”就品出了杨忠伟不经意的味道,未能给予杨高分。
斗茶是西湖龙井每年的传统赛事。杭州不仅客居了白居易、苏东坡这样的“别茶人”,也出现了以南屏谦师、参寥子为代表的“茶艺高手”。
这项赛事最初源自乡邻间的一比高下,之后成了展示当地茶叶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斗茶以“炒茶”为主要比赛内容,这不仅能区分品种的优劣,也能判定工艺的先进与否,最关键的是公开的赛事不仅可以对茶农的素质作出综合的评定,而且有助于促进茶农相互间的交流。
“茶王”出品的龙井没准还能当场拍出个“天价”。
2006年春天,樊生华一家搬进杭州城。在这片10多平方米的茶叶店里,一家子的起居都在店里和店面上方的阁楼。
如同过去妻子采茶、丈夫炒茶的模式,夫妇俩仍选择了妻子主管营销,丈夫负责炒茶技术的经营方式。
新茶尚未上市,店面顾客寥寥。樊生华反复强调,要不是儿子上学择校的需要,他们也不会搬到离桐坞村30里开外的杭州城。
他说,夫妇两人的生意可以维持日常开支,要谈到创收还距离比较远。
去年春天,西湖龙井上市后,樊生华在店门口炒了两把茶,一把来自西湖龙井一级保护区,还有的来自二级保护区。
樊生华并没有公示这两把茶孰优孰劣。
炒茶的能手,往往不爱说话。
即便脱离于“一级保护区”,在桐坞村村民的心目中,那老焦山上自家出产的西湖龙井绝非“二类”,它们均是顶级的上品龙井。
“顶级的上品龙井,一级产区就在我们这里。”如果游客到了梅家坞,或是上了翁家山,这样的招揽声不会绝耳。
有的时候,龙坞的茶农们会羡慕“狮”、“龙”、“虎”、“云”的命好,能有最多的主顾。
反过来,他们又会庆幸自家的茶园,正因为交通相对闭塞而有了生态上的优势,离天又近了一步。
很多西湖龙井的茶人不想卷入无谓的褒贬。仅仅做好茶,就像管好自己一样。
因为,“茶是天底下最不会说谎的”。
在夺魁“西湖龙井高级炒茶技师”后,樊生华的炒茶手艺赢得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称号。去年,他又获得了“西湖龙井炒茶大师”的美名。包括樊在内,获此殊荣的目前仅有3人。
樊生华将“非遗传承人”称号和获得的殊荣做成了店面招牌,也印上了自己的名片。
就在樊生华赢得“非遗传人”称号不久,便发生了一件震动杭州茶业的大事。
最后的茶树
与樊生华同属大师,经历也有一些类似,“腿脚不便”的杨继昌因为无法承受过重的体力活,就与炒茶结下了缘。
上世纪的1988年和1989年,杨继昌连续两年夺得西湖龙井评比第一名。除了炒茶技艺高超的老茶农身份,杨继昌目前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代表性传承人。
2012年年初,“炒茶王”突然病倒的消息传来,杭州市的业界措手不及。以他为代表的西湖龙井的炒茶技艺正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境地。
以杨继昌为例,生育三女一子的他只将衣钵传给了大女婿田建明。
前不久的3月20日上午,在女婿论及炒茶时,小个头的老头子一言不发,一旁的家人解释,杨继昌在发病后听得懂,但已经说不出来了。离开椅子的杨继昌,只能由家人搀扶着行走。炒茶闻名的厚实双掌只能挥手招呼了。
自从发病后,杨继昌就搬离了位于满觉陇的住所,住进西溪的儿子家中由儿子照看。
杨继昌住所附近,“满陇桂雨”小山坡上的3亩茶地里外缘,竖立着10多棵体型较小、尚未长成的“茶树”。得病前,杨继昌几乎每天都要上山查看,尚未长成的茶树是他最后栽种的一批茶树苗。待到这个春天,茶树上的茶叶尚未吐芽。
从城里来到郊外种茶,女婿田建明说是自己喜欢。但他知道,杨家的人工炒茶技艺有可能在他身后就面临“绝收”的境地了。机器加工正以不可替代的工业效率吞噬着传统的手工技艺。
回甘如何不变味
桐坞村的村民平均一年要泡上数十斤的西湖龙井。每一泡都自然有着味道。在村民家中的会客室,玻璃杯子、烧水壶,还有一桶山泉,那是招待客人的“标配”。
村民们喝的都是碎叶,那种在炒制过程中掉落受损的茶叶。经常品茗的村民说,龙井的茶水留在嘴里慢慢地会有“回甘”。
直到今日,西湖龙井不但是村民的“回甘”,而且扮演着经济支柱的角色。
中国茶叶博物馆馆长王建荣提供的数据是,西湖龙井核心生产区域6000多亩,每年仅产200多吨西湖龙井,比起全中国约180万吨的茶叶总产量,西湖龙井的量产弥足珍贵。
进入3月,城内的茶叶店和旅馆的前台便多了“新茶上市”的喜讯。西湖茶叶市场中也出现了“龙井新茶”的样品。
到了3月20日,桐坞村当地茶农们笑着回答我说,“我们刚刚炒制完第一批西湖龙井。”
经了火候的茶种为“龙井43号”。由于是西湖龙井中较为早熟的品种,开叶期早于“老西湖龙井”一周左右,它的早熟更是为了抢占市场。
在“旧坑”(数十年以上的茶树)和“新种”间,老茶农更青睐香味更好的“旧坑”,但想要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得不“快”字当头。
得名于天下的“龙井”,开始背负天下盛名之累。
这样的故事将继续发生在龙井茶农的一生中和龙井初长的春时。